他们自称制茶人,称他们的贸易为茶旅,称制茶为不泡,称布茶,称我们喝的茶为不茶,称茶汤。
布这个词一出来,好像场景就在眼前了。“汤”这个词一出来,我甚至讨厌人咽不下水。不,我们必须品尝这种汤以及制作这种汤的私人茶艺师。
茶馆在中国消失了很久,巷子深处的老舍茶馆成为了某个时代的记忆符号。还有散落的茶馆,以一种文人墨客润物细无声的姿态,静静的立在一个安静的地方,都是小门小面,没有奢华。突然有一天晚上,随着广东沿海地区的早午茶之风,茶馆从南到北一路如雨后春笋。此时的茶馆完全不像当年的骨架,文化成了摆设,而茶更像是生意的陪衬,乌龙闪耀,功夫不做。
但无论好坏如何传承,显然茶文化是可以找到机会重现,重拾旧山河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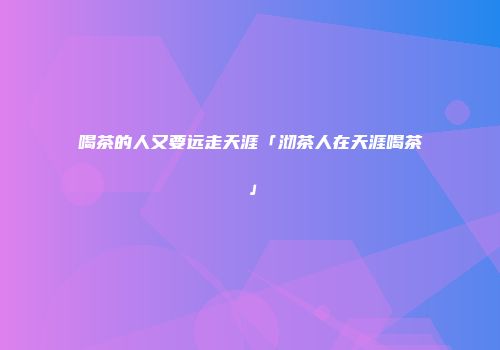
在茶馆和茶的繁华与沉寂中,有一群人,一直在默默耕耘。直到1999年,劳动部正式把他们列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 1800职业之一,我们才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,茶艺师。
在我们对茶一无所知的时候,茶艺师眼里只有沏茶水。当我们对茶有了更多的了解,我们不再满足于只是坐在茶馆里,而是想聊聊:请问茶艺师,什么时候提供上门服务?
对茶的关注,始于一年前一个茶艺师讲的故事。他一边给我们端茶——一套程序复杂的九曲红梅,一边慢慢讲信阳毛尖。
在河南信阳,腊月十八,外出经商的人返乡。从这一天起,亲戚们每天围坐在火盆旁喝茶聊天,成了当地的习俗。一只掉在窝里的老铜板烧着从山上砍下来的栗树,两根麻绳挂在屋梁上,一头扎着一个凹坑的大铜锅,一个绳结挂在人的头上。当铜锅里的水烧开的时候,女人把一撮第一年最好的毛尖茶扔到了众人面前的青花瓷大碗里。壶的壶嘴开了一点点,碗里的茶在翻腾。绳子空了,锅就升起来。当碗空了,再拉空绳。
我也想起了那天云南竹筒的清香:春天,新茶长出,新竹绽放。女人们砍下竹筒,采摘新茶,用铁锅炒熟,装进竹筒里。男人出门,女人给他准备干粮,拿出竹筒,扛在男人肩上。在森林深处,那个人又饿又累,生起了一堆野火。他把竹筒的顶端部分斜着切开,留一些茶叶在里面,把剩下的倒进切开后露出来的下一个竹筒里。茶会结束后,我舀起溪水,放在火上烧开。我呷了一口女人烘饼的香浓茶汤,累了,拿起了枪。又累又饿,我又砍了一根竹筒。
郑重声明:
以上内容均源自于网络,内容仅用于个人学习、研究或者公益分享,非商业用途,如若侵犯到您的权益,请联系删除,客服QQ:8411441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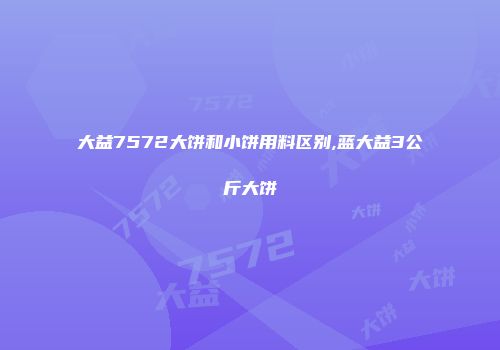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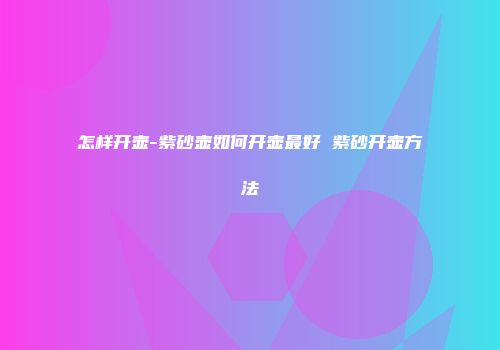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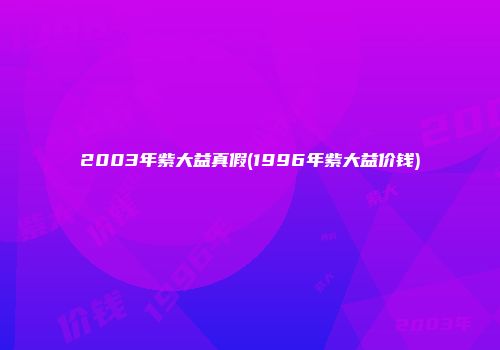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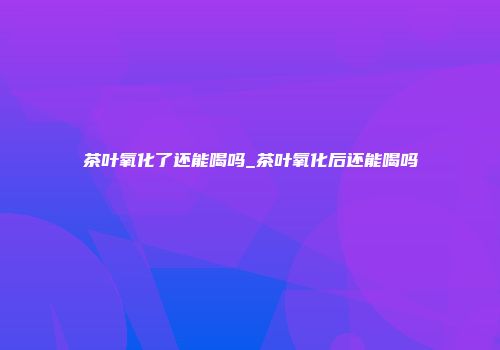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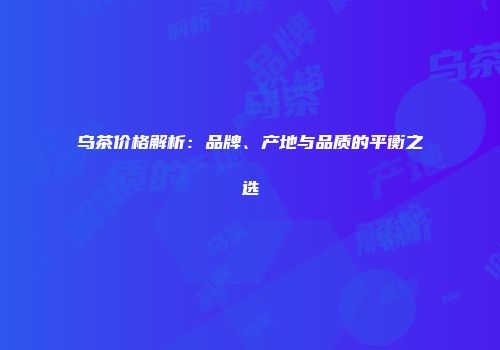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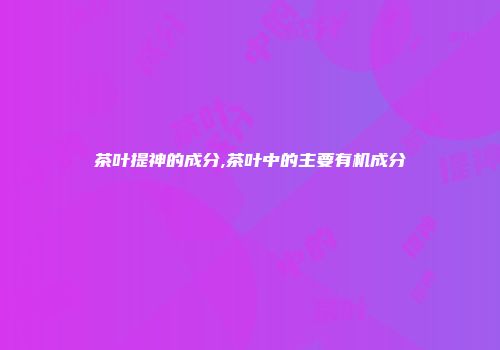


相关阅读